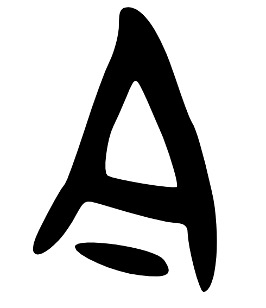关于王音创作的笔记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1]
在诗与叙事尚未分离的晨曦中,宇宙时序运行的薄雾保护着人与世界情感的原初形态,人类也依此而行,自然产生出富有节制的抒情和叙事。
作为人和外界联结的通道,诗和叙事似乎共同持有世界存在的真相。
也许此时,“画”与“写”还未彻底分裂开来,写“实”和写“意”也未区分开来,一切表达从属于人和世界关系的需要:描绘和庇佑融合在一起。
——
哲学家赵汀阳曾向王音谈起“今”的字源:它其实是个铃,铃的“舌头”在碰撞时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今”。
“今”:一个警醒的声音,一个时刻。
王音的绘画创作,回应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当代”:当这个时刻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它既包含了所有的过去,也是未来开始的征兆,它警示着:我们应该面向所有,犹如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
这个声音,有可能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的一切导致的回响。
——
如果将“今”之铃声延伸到表演艺术,我们的视线也许可以重新投向“传
统”的中国戏剧。在京剧那看似程式化的表演组织中,启发着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思考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感悟;而戏曲表演举手投足中对人性的洞察和提炼,不正呼应着《古诗十九首》对人类生存价值烛照的微光?
表演性的问题作为某种参照,对探讨如何在绘画的成规中“似演非演”似有借鉴的作用。如果说,在表演上和角色保持距离的“似演非演”,有效地同时表现了对象和表演本身,那么,在绘画创作上有意无意的间离,何尝不也是对自身位置的探寻和诘问,使得绘画过程不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当我观程砚秋、谭鑫培先生的剧照之后再看王音的某些画面,会浮现出“体态感”或“形状感”这样的词;同样,反思二十世纪现代西方戏剧的实践,比如:格洛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王音绘画的另一种状态:“剥离”,剥离多余之物。
究其实,王音的绘画总是逃离特定的、单一的经验状况,当我们面对这些绘画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更为复杂的“情动”和解读,而所有这些解读,最终都将是对意义的释然和偏移;进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王音在不同阶段的创作调整,也是在绘画中持续减去附会意义的过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这探索过程中,绘画的“技”与“道”的关系不断转换,从而滋生出种种凝炼而又层次丰富的“可感性的时刻”,持续让我们瞥见某种只有通过陌生化的经验,才能达至的人性中至为深沉、至为普遍的情感结晶。
——
我感到,王音近期绘画中的清朗之“象”,似乎回应着晨曦中的钟声。这是守夜者期盼的黎明,是某种深情厚意的凝聚物——出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是被遗忘的情感;这里面所涉及的情感线索和理路,因应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生发出不同的感触。而王音将绘画作用于人的方式重新归功于绘画本身谦逊的力量,这是艺术有可能成就的、和自然相似的、复杂而单纯的力量。
——
据说“象”这个字的本源,来自上古时代,那时,中原一带的天气还很温暖,黄河流域有不少大象。气候变化之后,大象南迁,只有“象”的意识留存下来。
通过“迹”而感受“象”,循“迹”而追寻那个消失的但实有的东西。
相比之前强调“地域口音”的实践,王音近来的工作,让我们无法不去思量和想象:当代绘画实践,有没有可能回应一种绘画中“共有”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借助充分的绘画实践我们可以感触到它——我们是否可以假定它为某种共有的、本源性的绘画意识?
就像我们今天可以体会到塞尚和董其昌之间某种遥相呼应的“画感”,或者,今天可以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造型和线条,体会到它们和早期文艺复兴绘画状态的某种空谷足音的神似?
一种共通的、看不见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东西。
一种凝炼的、原状的东西。
一种“象”。
关于绘画的共同经验,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共同经验。而艺术,在何种意义上,将是人类生活继续存在下去的需要?此时,我不时回想起王音所说过的:“绘画是重新组织生活的方式。”
——
“象”作为某种参照,对于我们探讨“共同经验”为何物似有借鉴作用。例如,“渔樵”之象,数千年来,不仅在中国文人画,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不断浮现,不断演化着。今天,当我们切入“渔樵”之象的内在精神,似乎也可有全然不同的形态可供联想和延伸。例如,本雅明笔下现代都市的“浪游者”(flanerie),以在都市丛林中“游荡”作为思想生产的方式;另一种时刻,贝克特笔下具有自我放逐感的“流民”,也可成为和“渔樵”对话的意象:
当我在外面时,早晨,我走去迎新太阳,夜晚,当我在外面,我也是如此……有生命的灵魂啊,你们会看到它们是相似的。[2]
也许,正是从这种“无为而作”中,艺术实践有可能驱近一种本源性的劳作,一种修复整体性存在的劳作,一种切入到生存基底之“象”,伴随着永恒的探索,和平静之下潜伏着的激进。
——
我发现这些工作的推进与演变,不断在接近某种类似“幸存”的特征,这是我最近感觉到的。[3]
艺术中幸存着什么?什么是幸存的艺术?是否有一天会因应我们和绘画的遭遇,某种表情、某个纹样、某块光斑、某种厚实的笔触,某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造型……会让我们出其不意地收获隐秘和复杂的情感经验,从而打开时间的通道,挽回被时代扼制的对人类生活的想象,以及“被粗糙的思想与观念的杂草所遮蔽着的‘内在理路’”呢?[4]
如果这个包含着“幸存感”的时刻,是一个涵盖所有过去,同时也是在变动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将如何穿透绘画的有限性?也许恰恰因为这种有限性,绘画才可以成为让这个时刻浮现的媒介。
而我感到王音是那么样珍视时间的馈赠,他唯一的依据,甚至只剩下手中的画笔。
——
犹如某种事件之后的幸存者,不再受制、纠结于当时环境给予的明确暗示,在这儿,首先,只剩下了“个体”——焕发出耐人寻味的多面性,或者,显现出如联体一般的个体集群;相应的,绘画也成为某种“多重变体”,蕴含着再次变化的期待,期待着,一旦某天,笔触和色调微调,她们就将走向另一个年华,走向某种残存的生存意识的再造。
在这阻断感伤的沉静中,画中场景让我们回到人类孩童时代的庄严和脆弱,在这之后,人类纯真的茫然一再被制度化为某种世故的表情,而这些绘画,不是为了挽回和再现某种表情,这些绘画,勿宁是为了探究这些表情如何重回无辜的造型,以此让造型成为一个个不拘于时代的“场所”,成为人类现时还存有自然和自在之处的见证。
胡昉,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