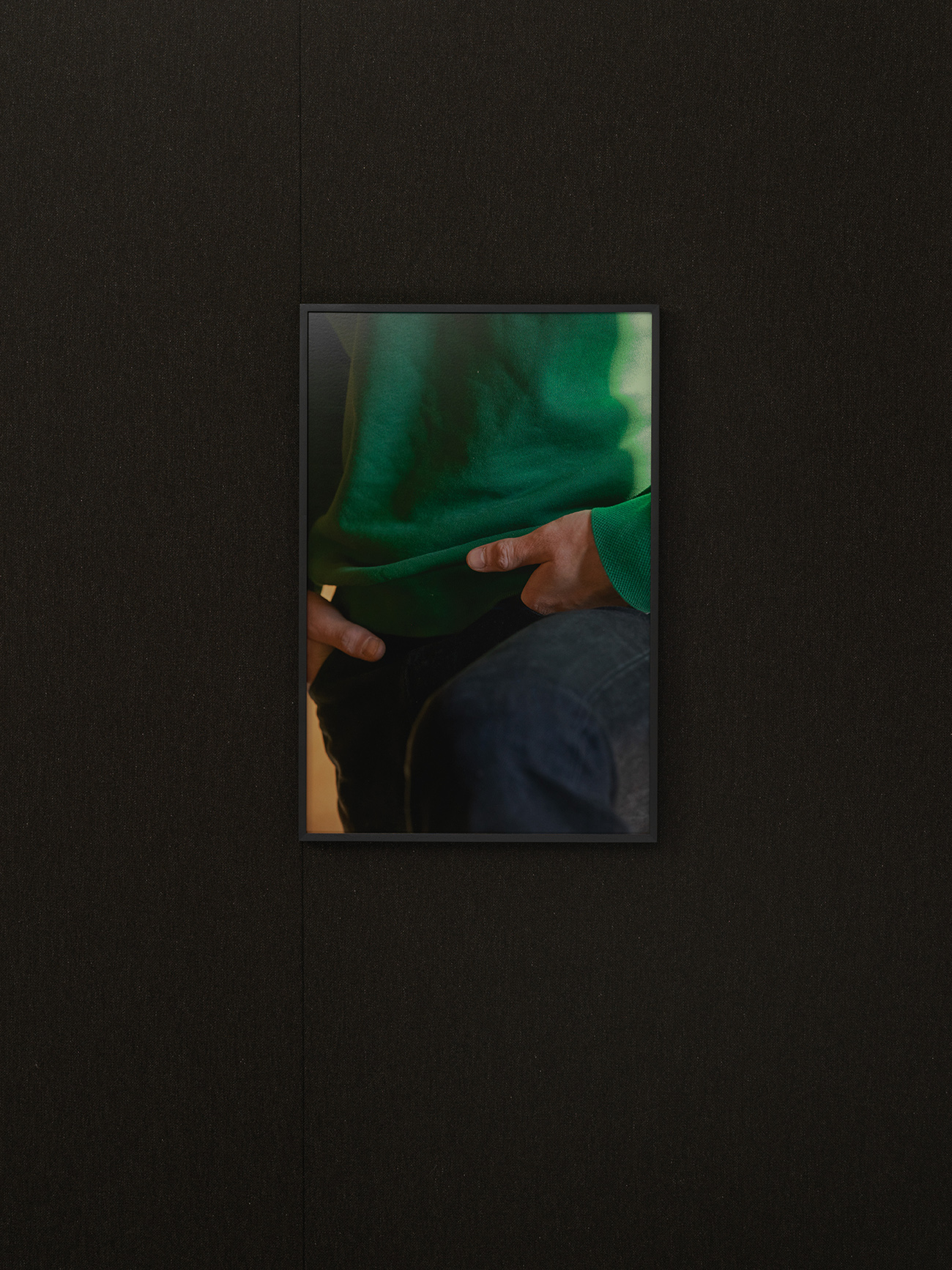傅丹
All work(只会工作)
2019
Peter Bonde所作的绘画;Heinz Peter Knes所拍的关于傅丹外甥Gustav的照片;Phung Vo手写的文字,纸上铅笔;墨丘利躯干大理石雕像(公元一世纪,古罗马);Nanna Ditzel设计的布料;Antonios Magoulas和Bogdan Ablozhnyy所作的绘画;Fred Fischer 和Uwe Trierweil设计的家具
尺寸可变









 威尼斯双年展2019年,绿园城堡(Giardini)展览现场
威尼斯双年展2019年,绿园城堡(Giardini)展览现场
傅丹
Suum cuique
2019
Peter Bonde所作的绘画;傅丹外甥Gustav的照片;Phung Vo手写的文字,纸上铅笔;据Franz Ehrlich的设计制作的椅子
场所特定,尺寸可变
在为威尼斯双年展2019“愿你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所作的项目空间中,傅丹在多位在世和已故的艺术家的作品之间搭建起精彩的对话,这些作品在保留它们自身特点和历史的同时,进入了一个祛除审美和意识形态纯粹性的空间。它们从维他命空间出发,在威尼斯双年展和其它展览中继续着,傅丹不断尝试这些要素,它们将如何和周遭的一切发生关系?在地缘政治的混乱和持续分裂的身份认同的纷争中,傅丹的项目探索艺术和个人的独立性如何可以拥抱集体精神的方法。
没有人会将激进的现代主义包豪斯学派与纳粹的文化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然而, 在历史某一次任性的转向中,包豪斯设计师弗兰茨·埃尔利希(1907-1984)(他自己也是集中营的犯人)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大门上镶嵌的一句德语“Jedem das Seine”设计了无衬线体(sans serif)。这句话源于罗马法律格言“suum unicuique”,原文为拉丁文,意思是个体获得其应得的权利。“各得其所”被纳粹盗用、曲解以传达犹太人的命运都是其应得的。傅丹的父亲Phung Vo用他所选的字体手书了这段文字,在这里,多层历史的牵连以及自身的身世交织在一起,同时存在,难解难分。
傅丹丹麦出生的侄子古斯塔夫是艺术家不时重返的缪斯。在《古斯塔夫的翅膀》(2012)中,我们看到年轻的古斯塔夫摆出古典的姿态,赤裸的后背凸显了其隆起的肩胛骨,它们看似一对天使的翅膀。在随后的《古斯塔夫的翅膀》(2013)中,男孩的身体被翻模,用铜铸成六块,然后再杂乱地焊接成一堆。如果说这件作品是某种“人终有一死”的提醒——年轻的身体被生活压碎,耗尽——那么《无题》中古斯塔夫的照片则展现了一个从容自信,自我实现的青年。这些照片由傅丹的爱人和合作者,艺术家Heinz Peter Knes拍摄,它们戏谑了时尚摄影的惯常手法,让模特参与其中,作为雕塑形态和亲密朋友对待。这些照片一部分指涉了Knes在90年代弗兰肯乡村地区拍摄自己青春期的兄弟姐妹的项目E.M.T. in MSP,当年的照片捕捉了他们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浮现的温柔情欲。傅丹的作品常常返观过去,而这里的古斯塔夫,作为年青一代的一员,成为希望的化身。
傅丹和丹麦艺术家Peter Bonde的关系可以追溯至傅丹的学生时代,当时Peter Bonde是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也是傅丹的导师,在他见证了傅丹一系列无法理解的学习“议程”之后,他在一封推荐信中建议傅丹应该放弃绘画。这封信后来成为傅丹的作品《自画像(Peter)》(2005)。Bonde对傅丹作品缺乏热情,作为回应,当时的酷儿艺术家傅丹在老师的画作中看到了过度的大男子气。时间和艺术的意识形态不断流转,傅丹在一些年后偶然看到了一幅Bonde的画并为之震惊。他访问了Peter Bonde的工作室,和当年的老师重新对话,邀请他的绘画进入到这个作品中。
Peter Bonde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展开“态势抽象”(Gestural abstraction,or Action painting)的绘画,注重绘画的过程性和行动性。近些年来,他采用了镜面箔片作为画布,镜面箔片既清晰地保留了绘画过程中的痕迹,同时也是暧昧的、并非具有明确指向的、高度抽象性的表达,当观众站在绘画前,观众也成为绘画的一部分,成为消溶的色彩的一部分。作为一位擅长色彩的艺术家,Bonde的绘画表面呈现出犹如在流动的空气闪现出微光的质感。
傅丹为这个项目而引入的布料来自Nanna Ditzel(1923-2005)——另一位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战后“丹麦现代设计”(Danish Modern)重要的女性设计师,藉此重新发掘了她具有历史意义的织物设计:Hallingdal。自1965年Hallingdal设计原型问世以来,丹麦Kvadrat公司至今仍在持续生产这款布料,且不断发掘色彩,成为广泛应用在各种项目和产品上的Hallingdal 65。它由羊毛和纤维胶两种材料构成,具有独特的双重性,两种材料互补:羊毛提供了完美的耐用性和适应性,纤维胶增加了颜色的深度。Hallingdal 65目前已发展出58种色彩设计,色调从中性的到强烈的,包括Nanna Ditzel最喜爱的色调:青绿和粉色。有趣的是,Nanna Ditzel曾经说过:“一个无时间性的设计就不会是一个重要的设计。”而Hallingdal 65也许将证明她自己说错了。
和很多20世纪的女性艺术家一样,Nanna Ditzel在现代设计中看到了民主和创造的动力,这和男性艺术家们媒介特定的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他们坚持在自治的纯粹性中实践,这或许是他们的特权,也可能是某种不幸。
傅丹所钟情的另一位设计师Enzo Mari则带来对设计极具批判性的视野。 “Enzo Mari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应该设计,终究,这是将自己从被设计中解救出来的最好方式”(G.C. Argan, 1974)。1974 年,Enzo Mari在Galleria Milano的展览项目中,公开了此展览项目里的所有家具设计的图纸,邀请每位对设计感兴趣的个体,亲自动手为自己制作家具,Enzo Mari 称之为“autoprogettazione”(self design,自行设计),藉由简便易行的材料和技术,Enzo Mari鼓励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来自行演绎、实现基本设计,在做的过程中可对设计具有更为切身的体验与认识,从而渐渐对设计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据“自行设计”的灵感,傅丹展开了一系列介于家具与雕塑之间的实践。
傅丹曾表示他将“用爱的军队攻击世界”,但他的军队是幽灵般的,包括历史中逝去的以及还在流动着的一切:弗朗兹·埃利希设计的椅子将与艺术重新对话而不再服务于纳粹的内部装修;古斯塔夫的重新归来是作为解放了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年;画家导师和学生之间看似不可能的僵局终被置之一旁;而从包豪斯以来的,致力于改善社会的现代设计以不同的变体进入到个人和公共空间的建构中。这些不同维度的区域和联系以不同形态交织着,经由生命编织的经纬,而共存于可持续对话的空间,成为塑造未来发生的事物的力量,回馈至不可预料的生活进程之中。
我并非想说,我所有的这些兴趣都是有意义的……通常唯有的直接联系就是通过我的生活……从遭遇我的任何事或我所遭遇的任何事。将所有这些都放在一起……这基本上就是我唯一所能做的事,而我必须相信,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傅丹,2018
文字提供:由观心亭基于傅丹工作室提供的文本编写
图片提供:傅丹工作室
©艺术家,观心亭,2019